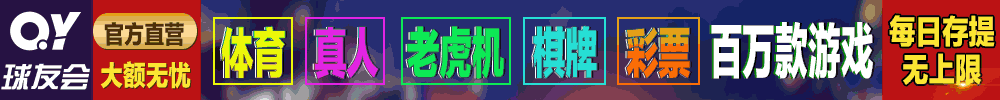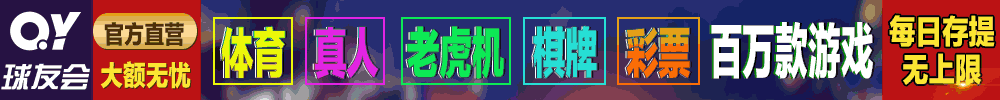妈,这个喇叭花可不可以吹?”
“可以吹。”
“会不会响?”
“会,今晚在你梦里响。”
“你骗人。你是小狗。”她笑着,就如那牵牛花开。
而阳台上,父亲爱怜地笑着,疼惜地抚弄着阿罗的软发。从春天到秋天,这里更番开着黄灿灿的金丝桃,亭亭玉立的紫锦葵,妩媚的虞美人,雍容的秋菊…还有许多可爱的不知名的小花。
是谁说过,这些美丽的花朵就是花的性器官?
又做梦了。
梦醒来,却是又一场秋雨。这雨总是不停地下着,在对面的观音山下落着,在眼前的这片草坡上落着。雨其实不大,却仍然潮天湿地,异常地湿润着阿罗的梦。
梦中的阿罗常常困在幽寂的冷雨中,那潇潇的秋雨。
阿罗一直固执地认爲,这秋雨是属于女人的。因爲它富于感性,空蒙而且迷幻,有薄荷的味道。
不知道爲了什麽,梦里醒来的她总是双手覆盖在她那无毛的阴牝上,轻柔如雨,竟如黄叶纷飞,盖在狭小的阴缝间。
而此刻,阴牝湿润,正如那秋雨。夜色漫漫,风也依旧,雨也依旧,而阿罗的心却有一阵的痛。
她害怕。她迷惘。
又是一阵雨来了,轻轻地敲打着这座城市,苍茫的屋顶,远远近近地,一张张屋瓦地敲过去。有如那古老的雷公琴,节奏细密,有一丝柔婉和亲切,似真似幻,就如此时悄悄袭来的这只手。
这是一只熟悉不过的手了。它慢慢地从阿罗的脚弯处,蜿蜒直上,在她白皙的大腿内侧稍微地停留片刻,就伸进了那潮湿的牝户内,轻轻沈沈地弹着,就好像那秋雨的零落,即兴地演奏着。
阿罗软软的腰就拱了起来。她迷惘的眼望着窗外那浮漾在屋瓦上的流光,听任那冰冷的手在腿间拂弄,而唇间如吟诗般的吴侬软语,就是江南夜莺在夜下的低声呢喃,心醉在这漠漠轻寒间。
她的小手一伸,轻轻擒住英挺之物,感歎着这物的强大和无情。然后,有一股凉凉的水意弥漫在空间,她能听得见自己沈重的呼吸,因爲那物沈沈的进入。于是有一曲耳熟的童谣夹杂着母亲吟哦的鼻音和喉音。
顷刻间,她泪如雨下。
那物进了又出,出了又进,重複着那份热的温存,而牝花也是开了又谢,谢了又开。
她纤细的手环着那坚健的背膀,承载着一波又一波的沖击。这一阵又一阵紧密的秋雨,就如那无数支急速起落的钉锤,直打得她是喘不过气来,她瑟缩着,战栗着,只是下意识地抓紧。
她的头发。
***
***
***
***
或许是瘦西湖的水吧。
阿罗有着扬州女人所特有的安恬和柔婉。扬州女人初看没什麽感觉,但那份淡然天成柔情似水的美,是经得起岁月细细的咀嚼,而且越嚼越能感觉出那种独到的滋味。
择很庆幸,能娶到阿罗这样美丽的女子。跟阿罗在一起,内心总是很平静,没有了工作上的失意和焦灼,生活静如止水。而阿罗的沈静和恬淡,总是在不经意间地柔情四泄。就连做爱,也是那麽的清爽,在斯文中透着丝丝的激情。
“列呢,又不在家?”
“是呀,我想还是你跟他说一下。在家里总比住在学校方便。”阿罗明丽的脸上掠过红晕。
“嗯,其实就要明年就要高考了,住在校里也专心点。”
“你懂什麽?你老是不在家,家里还是要有个男人比较好。”
“说的也是,我的娘子。”
择倾心于她的似嗔非嗔,她的秋波流转,还有不经意捋发时,间露的腋下的那丛毛,乌黑性感。
“去,老没正经。”
阿罗试图格开那只不正经的手,下体一凉,蕾丝内裤已被褪下,亮出了纤细的阴毛。她的阴毛明显是经过调理的,呈现出倒三角形,熨熨贴贴的,直指那桃源洞口。
阿罗轻呼一声。“啐,女儿在家呢。”
“她在楼上,没事。”
择迫不及待地沈了进去,厚实温热,这就是家的感觉。
阿罗轻轻地擡起了腰,这动作做了十几年,轻车熟路,但温故而知新,每一次做爱,总有新的感受。阿罗的鼻音很重,说话瓮声瓮气,加上她那一口软软的家乡话,别有一番韵味,犹其是做爱时发出的呻吟和喘息,更是平添几分性趣。
她闭着眼睛,长长的眼睫毛飘浮着兴奋的泪花。阴牝处香津四生,仿佛有水声浮浅,她摇曳的身肢就是水边的芦苇。
“嗯…………”
一湾细细湿黏的水自股间流泄,她的过分敏感决定了她的高潮总会过早的来到。这或许是缘自于她一贯的矜持和娇柔。
择有些欣喜地加强了他的力度,他喜欢这妇人做爱时所发出的那种幽幽的声音,似乎是絮语密密,令人陶醉。两人无间的情爱,合奏成一部无比优美和谐的乐曲,使得他们的心灵洋溢,每一次的上升和下降,都是那样的默契。
慢慢地,满室精液的味道,就像芳醇的醴醪出了气。
在沈醉中,择深深地抵在阿罗的阴牝,忘记了地球的转动和人世的尘嚣,在迷恋中,他发出了沈闷的呼喊。仿佛是一刹那,却又像是一个世纪,这日子竟是这样的美好,温馨,甜蜜……
这不是梦,阿罗在缠绵的做爱节奏里完全放开了自我,彻底地融合、溶化,感受着那令人怡悦的爱抚和那喃喃的絮语,她从云端里跌进了快乐的樊笼,她的温柔的葇荑紧紧地按在他的肩胛。
“择,我要死了……”
择提出了那物,晶莹,闪亮,这一刻,她真美,美得放蕩淫縻,美得惊心动魄。
***
***
***
***
隔夜的风雨洗净了山道上的尘埃,却留下了一层薄薄的露水,在道旁的小草上,树林中迷漫着白色的残雾,在枝叶间滑过,再逐渐消失在林壑深处。山间很静,连鸟声都是那麽轻柔,似乎怕惊醒了还在沈睡中的早晨。
“傻女儿,也不多睡会儿,非要跟爸出来晨练。”
择爱怜的拭去端头发上的晨露。
每一次回家,他总是到后山来走一走,只因爲走在这里有一种极其熟悉的感觉。脚底下的青石板路,白云深处的庄严的寺院,山上的针叶树以及道旁盛开着的淡紫色的花朵,总是若有若无的碰触着心底深深的乡愁。
“爸,你这趟要回来多久?”端幽幽地看着身边伟岸的父亲。端长得很美,每每轻笑时,鹅蛋形的脸的左侧便旋出浅浅的洒涡,时隐时现,盛着一些快乐,盛着一些忧愁。
“也就几天吧,你知道,爸总是没空。想想真对不起你们。”择是个资深记者,精通阿拉伯语,常驻埃及开罗。
择继续沿着山道上走,几株枫树参差地站在道旁,清风徐来,一树酡顔,令人欲醉。
“晓来谁染霜林醉,点点是离人泪……”端嘴里低吟着,美丽的眼角竟有泪花闪动。
择心中一动,回头望着她,端正癡癡地看着自己。
“女儿,怎麽了?小小年纪竟有这麽多感触。”择有些内疚,毕竟自己离家良久,关心女儿太少,太少。
“爸,你就不能调动一下工作麽?”端擡着头,她的声音有些沙哑,有着花季少女不应有的苍凉。
“过一阵子吧,我已经把报告送上去了,唉……不过可能很难。”择有些无奈,缄默地把目光投向丛林深处。
“女儿,在老家还有一种乌桕树,比枫叶还小,可是红得比枫叶更豔,一夜风霜,会使它红得更美,就好象醉酒的佳人。”
择想转移话题,却见端把脸别向一边,几颗清泪夺眶而出。
“傻女儿,怎麽哭了?哪里难受,跟爸爸说说。”择有些手足失措,青春期的少女是未知的谜是不可测的天。
“爸……我爱你!”
“我也爱你呀,女儿。”择亲切的抚摸着端那如丝绸般细腻光滑的长发,怜爱之心既起,愧疚之情已生。父爱关心太少,一直是他心中最最深深的伤痛,多少年来在外漂泊的他总是浸浸然的心碎。
“不,爸,你不明白……你不知道……”端抑制不住泪水的飘零,哀哀的看着毫不知情的父亲。
***
***
***
***
那日已近中午,端身体不适,提前回家。
“列,妈求求你……你不要这样折磨自己,都是,都是妈不好……”
端听到了母亲的啜泣。今天怎麽了,妈和哥哥都在家里?端奇怪地听见了列的哽咽声。
“妈,我们不能再错下去了,错不在你,是我的不对,我不该……”
端的心忽然变冷,发生了什麽事情?
她放慢脚步,缓缓步上楼梯。眼前的景象淫縻之极,母亲不着寸缕,瘫倒在地板上,美丽的胴体白得耀眼,三角地带的阴毛蓬乱无章地堆放着。
而可怕的是,她的哥哥列跪伏在母亲的胯间,发疯似的扯着自己的头发,他的下体裸裎,下垂着的阳物大得惊人。
“我原来只想……原来只想回家拿些换洗衣服,可,可我控制不住自己……妈,你太诱人了……”
列泣不成声,双手捂着脸庞,显是悲痛不已。
“这都怪妈,天太热了,妈以爲不会有人……就没穿衣服。列……其实你也不用控制自己,老是憋在心里对身体不好。尤其是你刚刚要发育。”
母亲的手好白,落在列的发上更是黑白分明。
端忍不住打了个寒噤。母亲那纯洁雅丽的面庞,蕩漾迷人的笑涡,举手投足间的优美动律,曾经是多麽的叫她妒忌。可现在呢?
端忽然有点恶心。圣洁高贵的神像在倾刻间轰然倒下,端的心底感到万分的惶恐和惊慌。
“我对不起爸爸,对不起你,对不起所有人……”
母亲捂住了列的嘴,柔声的:“列,你没对不起任何人,只要你不说,我不说,又有谁知道呢?”
列擡起头,眼神中满是矛盾和迷茫,“是吗?是这样吗?”
他癡癡的望着眼前的这朵美丽的云,他真想离开这世界,去另一个地方寻找梦想中的幸福。
母亲亲吻着他的手指,他的眼睛,然后两唇相接,胴体交合时发出了嘶嘶的响。在这片可怕的黑色的浪潮里,他们如醉如癡的遨游。
端流泪了,她默默地撚着衣襟的下摆,人与人之间最真的东西消失殆尽,善良呢,就好象喂猪的糠秕在纯洁的天空中散扬。心,发霉,澎湃的血液,汙浊无光。
列就像一头疯狂的野兽,张扬着锋利的脚爪,撕扯着身下的猎物。
这世界好黑,需要一盏荧灯!
而母亲强烈的痉挛着,亢奋着,在本已狼籍的地板上扭缠着,声嘶力竭。阿罗抑制住那种无端的烦躁,调理着思想的弦线,但那受了潮似的弦线只是发出微弱而杂乱的嘈音,她已经无法将这些散漫的音符组成乐章——时间像一条蓝蓝的河流,歎息着,迅疾地、默默地流经她的空旷的心田,流向无垠的大野。阿罗拉开窗子,风挟着片片落叶欣然地掠过她的香腮,淡淡的夕阳堆一院阴影,又快黄昏了呢!他怎麽还不回来?
凝视镜子里的自己,脸颊晕红,似羞还羞,秋波流转,竟如初恋一般。她一直引以骄矜的是,自生育以来,身材依然是那样的曼妙婀娜,皮肤依然是那样的白皙细腻,以致于常常令课堂上的那些男生们癡迷不已。
她缓缓地擡起手,解开了系带,露出了精美的胴体。乳房不大,却依然圆润丰挺,不因岁月流逝而有所下颓,反而张扬出少妇特有的风韵与情思。
她微闭着眼,抚摸着樱红的乳蒂,顺着纤细的曲线往下走,逗留在了那草丰水足的溪谷,瞬间,有一股颤栗流经了全身。与手指频繁快速的穿插不同,空虚和寂寞正在侵袭着她的情思,她渴盼着,嘴里喃喃自语:“列……啊,列……”
而窗外,月亮升起来了,淡淡的,惨惨的一弯问号。
电话响了。
阿罗的动作凝固了,脸上的表情依然沈缅于极度性欲之中,她抽出了手指,一汪清泉飞泄直出,她放在嘴里舔了舔,拿起了电话机。
“喂……”她发现自己的声音竟有些沙哑,嗲得厉害。
“喂……怎麽不说话?再不说就要挂了……”
对方还是迟疑着,缓缓地,有那麽一会儿,她差点要挂了。
“妈,是我……”
“啊!列……你在哪里?妈……妈,好想你……”阿罗能够清楚地感觉到阴牝的潮湿和温热。
“妈……听说,听说……爸,回来了……”
“是呀,你……要不要回来看看?他过几天又要出门了……”
“他在吗?我……我想跟他说话。”
“没,没有……他带你妹妹去新华商厦买衣服。你……你在学校吗?”
“是,是在学校。妈……那我要挂了……”
“别,别挂。列……你回家吧……咱们有话回家好好说……嗯……”她喜欢听他的声音,就好象流水受了风的鼓蕩,而芦苇正在倾诉它的寂寞。
“好……好吧。”
列想了好久,起伏蕩漾于他内心的愁绪,有了些彀纹和潺湲,毕竟妈是爱他的。
***
***
***
***
记得那一天,列和母亲去姥姥家回来。
雨下得好大,听得见雨点敲打车窗的沙沙声。车窗外面,高速公路的两侧,那些在白日晴空下一垅一垅翠浪摇蕩的麦田,一方一方波光潋滟的水塘,还有那弯弯的桥、亭亭的竹,以及兀立于坟场上古老的银杏树,依偎着河流村舍的美丽挺拔的水杉树,全被这晦涩的风雨消溶了。
喝了些酒的阿罗霞光满面,神情专注地望着窗外,显得异样的明媚迷人。
列第一次这样凝视着自己的妈妈,陶然于母亲那绝世容光中。他的心跳突然加速,嘭嘭嘭,就如那午后的雷。
记忆中的母亲端庄娴淑,典型的江南闺秀,温柔秀气,一直是列心目中一尊高高在上的女神。
这江南酝酿十几年的女儿红呀,真烈。列是第一次喝酒。
“列,今天姥姥生日,你就喝点,没事。”微醺的阿罗忘了儿子还只是高中生,附合着那些亲戚。
列直到上了车还是心跳得厉害,他能感觉到口干舌燥。他摸索着,探身想拿母亲身边的袋子,可是他没有拿到矿泉水,却触摸到了母亲大腿的温热。
阿罗嘤咛一声,没有动,显然还沈浸于遐思之中。车速越来越快,而窗外原本连绵不绝的雨已停止,阳光潋滟,抚在脸上就如阿罗温暖的手。
列扶着身子娇软的阿罗,打开家门,母亲一下子瘫在沙发上,酡红娇羞的脸蛋比墙角盛开的非洲凤仙更是璀璨夺目。列也有些恍惚,满室有阵阵淡淡细细的香气,氤氲着,有做梦的感觉。
至今仍使列心中有一种撕裂心魂的隐痛,惊悸,悲喜,如巨浪拍打着海礁,从此他常常失眠,一夜又一夜。
这一切又是怎麽开始的呢?
列坐在孤独的黑暗中,听着微风在窗外急行,从窗帘隙缝的微光中,默默凝视着母亲那美丽的脸庞,如流云一样柔软浓密的长发,孔雀开屏地散落在沙发的扶手上。
“时常,我静卧榻上/一无所思或耽于冥想/水仙花儿闪现于我内在的灵眼之中/乃是幽独的人儿享到的清福:我心遂充满了欢慰之情/和水仙花儿一同舞动”列迷茫中忽然吟出华兹华斯的诗句,他双腿一软,跪在当地,颤抖的手抚摸着那滚热的胴体,他看到了,看到了……
浅粉,暮春的鹅黄,同樱桃颗一般的绯色,所有的美丽,都云集于一个人身上,他的母亲——阿罗。
那天,是列一生一世也忘不了的,像梦,却又这样的真实。他哭了,漫天湿地的泪水如雨点倾泄在这豔阳春暖,百花争妍的河谷。
这是他的破茧之旅。十八年的青春作古岂曾想像竟是这般的沈痛?
他怒吼着,沈入了这潮湿的谷地。一路鸟语花香,蜂唱蝶舞,他走过树荫曲径,踱过断桥流水,越过峭壁高峰,后来又沿着一条小溪,努力地登攀。
汩汩的泪水和涔涔的汗水交杂着,粘白与粘白混合着,这是条潺潺的小河,蜿蜒着,不知流向何方?
阿罗闭着美丽的眼睛,她细细品味着这孽欲的成熟,对于这种感觉,是那样的根深蒂固。她做爱时惯有的鼻音在轻轻浅浅的呢喃着,如檐间飘洒的夜雨。
阿罗的眼睛睁开了,仍旧那样的清澈美丽,只是惘然中有一泓沈寂的水,她怔怔地望着软趴在自己身上的儿子,她最锺爱的儿子,而心中的五味杂陈就如水银泄地。
“列……”列的肩膀上齿痕斑斑,是她咬的,素来娇气的她竟是这样凶狠?
“妈,对不起,妈妈……我禽兽不如……”
列声嘶力竭,梦靥是冷酷的,世界是苍白的,他瘫软在地,痛不欲生。
“怨妈妈,妈……不该让你喝酒,尤其是……”尤其是这极品女儿红是她家族特有的陈酿,里面渗杂罂粟粉,有催情作用。空气中有淫縻的气味,阿罗裸裎着下身,阴阜微隆,爱水淋漓。
她不知道怎麽安慰儿子,其实就在那一刻,她是清醒的,她本可以阻止的。
“不!不!我错了……”
列惨叫着,奔出了家门,那身影寥落,充满了无边的绝望和悲哀。阿罗痛苦的闭上了眼睛,又有谁愿意,是命运安排,还是个性使然?她早已坠落乱伦的渊薮。
那一天,父亲拿出了女儿红。
“乖女儿,这是专门爲你準备的。”
“爸,这酒很烈的,我还要回家呢。”
“没事,你的酒量向来是家里第一的。”父亲说的没错,婚前的阿罗是家族中最会喝酒的。
“来,再喝一杯,孙子。”列有些腼腆,但还是喝了,这是外公的酒,不能不喝。
“爸,他还是孩子呢,你要灌醉他吗?”阿罗嗔怪地白了父亲一眼,夺下了列手中的酒杯。
“列,你不要再喝了,我出去一下。”她感觉尿意频频,酒到胃里就化成了分泌液,压迫着她的膀胱。
她有些踉跄,手扶在茅房的土灰的墙上。
“妹子,这麽多年了,你还是跟从前一样漂亮。”一双熟悉的手从后面环抱住她,她知道是大哥。
“哥,别这样,我孩子都那麽大了,妹妹老了。”
“不,在哥的眼里,你永远是那样的新鲜……真香。”他嗅吸着她颈边的云白,解下了她的裤腰带。
“不要,哥,不要……”
“好妹子,你知道,你嫂子管得严……这些年,哥好想你……”他的硕大已经顶进了她的溪谷。
“啊……不要在这里,哥……”
“好妹子,香香妹子,让哥来通通你的小屄……”他依然是那样的强大和粗鲁,阿罗哭了。
“别哭,妹子,真好,哥好舒服。”
“慢些,疼……”
“你知道吗,等会儿二弟要赶回来呢。”
“啊,他回来干什麽……”阿罗被顶在墙壁上,只觉着身子不是自己的。
“他要回来干你呀,妹子,大家已经好久没在一块了。”
是呀,多久了?有十几年了,当年跟着择漂泊远方不就是爲了躲避麽?此刻她的阴户里热乎乎的,这种强烈撞击的记忆好生熟悉。
“嘿嘿……你的屄好紧,就像没生过小孩似的……”
大哥还是那样恬不知耻,这夺走自己贞操的混蛋,可爲什麽自己却不恨他?莫非自己……阿罗连想都不敢想。阳光从罅缝里漏了进来,照在两个纠缠不清的胴体上,游移不定。
“大哥,好了没有?我要进来了……”
是四弟的声音,怎麽?他不是去温州了?
“好了,快了,你再忍一忍。”
大哥加快了节奏,力度更加强烈。
“他怎麽回来了?”
“是妈妈叫他回来的,你忘了,他可是他*的贴心宝贝。”
“啊,你再插深点,到了,到了……我这可要死了……”阿罗只觉得身在云雾中,轻飘飘的。
“三姐,你可真美。”
什麽时候,四弟也进来了?
“啊,别弄那儿……髒……”
“嘻嘻,又不是没弄过,姐,真紧。”
阿罗夹在两人之间,整个身子竟然不着地,她嘴里哼着,多少年了?往事如烟,却不曾消散,曆史重演,一幕幕的袭来。四弟仍如初次那般地勇猛,乳虎下山,热情如火,比早暮的大哥有劲多了,阿罗在晕眩中,笑了。
这时,二哥走了进来。
***
***
***
***
阿罗仿佛又听见了绿叶丛中紫罗兰的嗫嚅,芳草里铃兰的耳语。
她有些兴奋,如初恋的少女,娇羞如水,压在眉梢的那层厚厚的灰黯色的云在转瞬间化爲如纱的轻烟,如酥的小雨。秋瞳如剪,贝齿如玉,唇角边两颗轻圆的笑涡,吹弹得破的肌肤,镜子中的阿罗轻笑出声,这是“水晶般的笑”。
列是初升的太阳,是幻想的泉源,恍然之中,一个十八岁的健美少年向她走来,一股爽朗新鲜之气扑面而来。正如睡过一夜之后,打开窗户,冷峭的晓风带来的那一股沁心的微凉和葱笼的秋色。
他目射神光,长啸生风,她依稀间能看见他血脉里奔流的鲜红血液。接连数十日的淫雨菲菲,该是风和日丽的时候了!
阿罗心想,我是不是有病,嗜欲的饑渴,情欲的纠缠,沖动的驱策,野性的引诱,干渴的阴牝总是期待着秋雨的殷湿?
幻想,狂热,苦恼,以及烦闷,如苍蝇落于蛛网,愈是挣扎则缚束愈紧,乱伦的绳索早已束紧了她如雪如玉的颈脖。
“再来一次又何妨?这样又伤了谁呢?”
上帝造人也造成了人类的乱伦,阿罗恨恨地想。要紧的是快乐,而不是受苦受累,到了人生的最后那一刻,灵魂像蛾之自蛹中蜕出,脱离了笨重躯壳,栩栩然飞向虚空,生命的意义从此完结并轮回延续。
“妈,在想什麽?”
列站在身后,有力的手强劲地抱着她纤细的腰肢,她一阵激动。
“我想你,好想你,你回来真好。”
阿罗转身凝视他,阳光健康是他的本色,只是厚重的唇边多了一丝忧郁,她的心一揪,有点疼。
“妈,你真美。”
列拥吻她,樱唇如雨般湿润,有柠檬的芳馨,带着微微的涩苦。
阿罗一阵感动,体软如绵,心如鹿撞,更如初经人事一般。
“嗯哼……妈好甜……”
爲什麽,乱伦的果实如此酸涩,可自己却甘之如饴?
欲火焚身的阿罗擒住了那物,粗犷博大,她害羞地想,放进去的感觉真好!
狭小的房间里充满了一些奇妙的声音。列的抑扬顿挫,长短急徐,如风的低吟,雨的轻唱,有着神奇美妙的节奏,且不理它是以几分之几的拍子,阿罗更喜欢牝内水溶溶的模样。
“啊……”
阿罗配合着列的颤动,起落着,汲取着母子情爱的精华,这声音欢快响亮,有母亲的嗫嚅和儿子的低喃。
列驰骋着,如草原飞快的烈马,踏入了轻浅的小溪,不知怜惜,肆意淩虐。
他颤抖双手,摸向了那段颈白,“妈妈,妈妈……”他的手臂是那麽有力和坚定,他的眼神在疯狂中带着绝望。
阿罗兴奋的瞳孔光芒渐渐,渐渐的消散,她笑了,眼睛里泪水淋淋,“好儿子,谢谢……”
此刻,窗外的风雨停歇了,被风片撕碎,一切複归平静,阿罗听到了天国里响彻着“归去来兮”的梵音。
列静静地看着母亲安详的笑容,她真美!美得清盈,美得深邃而神秘。本来她的降世就是一次偶然的驻足,列一直坚定地这样认爲。
他爱着母亲,深深深深,刻骨铭心。
“妈……妈……”
他深情的呼喊着,颤抖的双手沿着母亲玲珑的曲线,迤逦着。这本就是一场充满悲剧意味的故事,本就不该发生在他们之间,可它偏偏活生生的亮裎在他原本稚嫩的面前。
“妈,这是我爲你準备的衣裳,你瞧,多美!也只有你才配穿它。”
列缓缓地给母亲穿上了藕灰色的西式衣裙,又给她挽了个高高的发髻,高贵端庄,文雅娴静,像一只美丽的白天鹅。
“妈,儿子陪你去,来世,来世,咱们做夫妻。”
他慢慢地躺在母亲的身边,紧抿的嘴角边漾起一朵美丽的微笑。暮色渐浓,墨黑的天边,缀上了苍白的星点。远处传来了沈重的鼓声。归于岑寂。
***
***
***
***
择坐在女儿的旁边,硕壮的身躯坐得笔直,似乎在专注的听,又似乎并不在听,深沈而哀痛的目光投向前方,窗外飞旋的雨点和夜光交织出含蓄而豔丽的图案。
他的脸毫无表情,才那麽几天,他的鬓角已是一片斑白。
端拉上了窗帘,黑暗就像巨型的蝙蝠,吞噬了一切有机的生命,死亡原来竟是这样的简单。
路过的车灯透过纱帘在墙壁上投了一些活动着的,古怪的阴影。在狭小沈闷的房间里,端沈郁的目光逐渐的清澈起来,她侧过脸望一眼父亲,择依然是那一幅表情。
雨点敲击窗户的声音很清晰,单调的,酷似蚕食桑叶的沙沙声,令她的思绪飘飘忽忽进入了一个空灵轻曼的世界。她仿佛看见,生命之蚕怎样一口一口咀嚼着常绿的岁月之叶,怎样一次又一次蜕变、重生,在空前的苦难中崛起。
“爸!”
她突然叫了一声,很轻但是很轻晰。
择望着她笑笑,惨淡,寂寥,苍白无力的,“我没什麽,你睡去吧。忙了几天,你也累了。”
“爸!……”又叫了一声,她真想拥抱爸爸,但随之她发出了一声微微的歎息。
“小孩子是不可以垂头丧气的。端,一切都会过去的。”
端惊喜地发现父亲直接的叫她的名字,她的眼睛睁得浑圆,美得凄凉惊豔,在这秋雨的夜。
择的眼睛不大,眼皮似双非双,似单非单,瞳仁很黑很深,在那里曾经蕴藏着执着的热情,充盈的活力,可而今,平添了几分忧郁和孤独。
四目交融,端像不会说话了似的,一丝喜悦在泪水中迸发:“爸,爸,你终于肯跟我说话了。我真,真高兴……”
“女儿!”
不知爲什麽,择又突然改了口。
“爸爸……”
“嗯?”
“我想……”她纤弱的葱指下意识的在桌子上划着,“想跟你说话。”
“不是在说麽?”
“是的,在说,可是,我想说的是,是……”她凝视着择,心里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。
“我想说你就像一个人——不,是那个人就像你……”
端嗫嚅着,有些语无伦次。
“我像哪一个?”
端闭上眼。睡梦中白茫茫的雨雾中,一顶红色的油纸伞飘然而至,伞下的他轻轻的对她笑着,如绽开在一派温馨中灿烂的蔷薇花,远离了风雨的凄凉。
她真想大声说,爸,你就是我阴冷沈湿的记忆河谷中那块温暖而又坚实的岩石!
她突然站了起来,颠三倒四,语无伦次的把沈埋在内心深处深深的思念喃喃的诉说,她不知道自己说清楚了没有,说了几遍,也不知父亲是否理解了她的那份刻骨铭心的相思。情感的渲泻原本就藏在一堆杂草中,少女特有的娇弱和羞涩使得她无法理清这些杂草。
但是自始自终,择没有说话,只是默默地看着她,任她东拉西扯,辞不达意的倾诉着。他一直在听,严肃地,默默地在听。在这个惊慌失态的女孩子面前,他显示出一种镇定的力量,一种岩石与山一般的可靠与慈父般的安祥。
后来,她说完了,像地狱里的小鬼一样,听候裁决。
他依然不出声,似乎还在听,等待下文。时间像静止的大海,瞬间变成了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