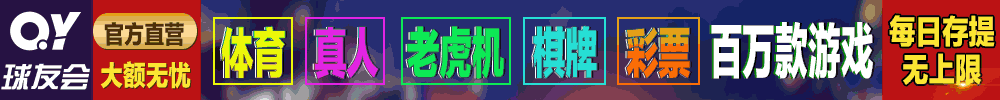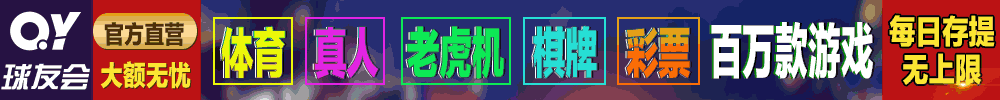「吱嘎,吱嘎」,京城卫府大宅的角落里,一间小屋内传出阵阵织布机的声音。
月娘的全部精力,都在眼前的这台织布机上。
她正在爲夫人赶制一匹绣锦,用来铺就夫人的高床软榻。
她生怕织错了一行,这匹锦缎就会废掉,之前的功夫也就白白浪费了。
月娘的手艺,是卫府所有织娘内最高明的。
经她的巧手织出的锦缎,凤可飞天,鱼可入水。
一切都那麽精巧而栩栩如生。
而她的手,一如她的手艺。
洁白纤长,柔若无骨。
如果不是她的出身低微,任谁也看不出,她只是卫府的一个纺织娘。
那双手虽然每日里都在纺织裁绣,却依然细腻柔软,不像是双下人的手。
而她的人,也正如她的名字。
比起天上的明月,她的眼睛更有光华,她的微笑更爲皎洁。
月娘今年十五岁,她的娘也是卫府中的纺织娘。可在去年,她娘便已咳血病死了。
从那之后,月娘便独自居住在这间小屋内。
卫府里的所有人都说,月娘是美人薄命。
她出生前,爹爹就被采石场的炸药炸死了。
现在连娘都死了,今后不知道会配给哪个小厮做老婆,真是糟蹋了她那副仙子般的脸蛋。
月娘不理会那些私语风言,只是认命地,每日里织着她的布。
似乎她的人生,都能在那一匹匹的锦缎里开花结果。
似乎她的命运,也都能在织布机单调乏味的吱嘎声中欲语还休。
今年的夏天格外地闷热。
尤其是京城,灼热的空气,似乎要把天地万物都烤着了火。
就连枝头上的知了,也声嘶力竭地喧噪着,像是在发泄着酷暑带来的不适。
月娘上身穿着薄如蝉翼的白色开襟小衣,下面是同样质料的及踝亵裤。
她身边摆着一大盆清水和一条手巾,每当热得受不了的时候,就用手巾沾点水,擦擦身上脸上的汗。
手巾上的水和身上的汗水,一起浸透了轻薄的小衣。
小衣贴着她的身体,月娘那身子玲珑起伏的线条,就被勾勒出一个清晰的轮廓。
有时她过于沈溺在自己的活计中,忘记了擦拭汗水。
晶莹的汗珠便顺着她的脸颊和脖颈,流畅地滴落在干燥的织布机上,滴落在饑渴的地面上,瞬间被吸收殆尽。
几缕乌黑的头发,贴着她的额头和两腮,衬着她绯红的俏脸,诉说着一种说不出的诱惑。
月娘自己不知道,当她的身体随着织布的节奏摆动时,她高耸的乳房也随之跳跃。
小巧秀气的乳头,便倔强地顶着汗湿的小衣,形成一个明显的凸起。
而那嫣红的乳晕,也透过洁白的轻纱,妖娆地展示着少女的风情。
月娘看看门闩,早被她闩得死死的,窗子也关得严严的。
这房里只有她一个人,穿的少些也不怕。
她也是急于赶工,想趁着这相对凉爽些的夜色,尽快把这幅锦缎织完,换夫人一个满意的微笑。
所以她不会想到,就在对面那纸糊的窗格后面,有两对几欲喷火的眼睛,正透过被捅破个窗纸,在窥探着她的一举一动。
「不行了,只能看不能动,我要受不了了!进去把她干了吧!」其中一个叫铁牛的偷窥者,压低了声音说道。
眼见着那对白兔般的乳房在眼前跳动,铁牛裤裆里的那根东西涨到生疼。
他不解恨地用手搓弄了几下,却像是隔靴搔痒。
真想马上沖进去,把月娘压在身下,狠狠地操弄她。让身下这硬邦邦的肉棍,不再那麽疼痛。
「别急,万一她叫起来,卫府人尽皆知,还有什麽可玩?」另外一个叫做王大的偷窥者,裤裆也早支起了帐篷,却还明白轻重。
这两人都是卫府的长工花匠,平日里对月娘的美貌,早就垂涎不已百爪挠心,经常用言语去逗弄她。
可心高气傲的月娘,从来不理会他们,让他们又恨又爱。
这两人早就在背地里讨论过月娘的身体,过足了嘴瘾。
更是在夜晚中,想着月娘的模样,做足了春梦。
「稍安勿躁。我这有好东西,一会儿等府里人都睡过去了,拿这个放倒她。到时,咱们想怎麽玩就怎麽玩,你急什麽!」王大从怀中,掏出一支小竹筒模样的东西,淫笑着说道。
那是他从市集无赖手中买来的迷烟,专门用来打家劫舍,奸淫妇女所用的道具。
铁牛眼睛一亮,继续靠近那窗格,耐着性子向屋里看去。
好饭不怕晚,这美人儿,今夜注定要被他们吞噬的。
更夫报了三更,卫府万籁俱寂。
几乎所有人都已睡下,只有这房内的机杼声,还在机械地重複着。
月娘又热又累,也打算再织完最后一寸,就去睡觉了。
王大看到她已有倦意,忙不叠把迷烟吹了进去。
不易察觉的迷烟,无色无味,悄然弥漫在月娘周围。
月娘不知道爲什麽,她今天觉得特别累。
手中的节奏渐渐迟缓起来,眼皮越来越沈重。
几乎没什麽预兆,她就突然昏厥一般,俯倒在织布机上。
「月娘,月娘。」王大狡猾地低声唤她,怕她没被彻底迷过去而坏了好事。
见她一动不动没有反应,才对铁牛使了个眼色。
铁牛兴奋地沖上去,用一把匕首,小心地透过门缝,一点点拨开了门闩。
门开了,两人飞快进入房间,回身又把门重新拴好。
现在,是时候享受这美体的盛宴了。
王大一把抱起她柔软的身躯,把她放倒在睡觉的小木床上。
爲了保险起见,他还拿出事先準备好的麻绳,将她的手捆在床柱上。
又一把撕扯下她的小衣,胡乱塞进她的口中。
并解下自己的腰带,蒙住她的双眼,防止她半路醒来之后的反抗和呼救。
铁牛看着烛光下这具白嫩光洁的女体,也抑制不住地靠上前,发狠地扯下月娘的亵裤。
现在,月娘已是不着寸缕一丝不挂地,躺在两个男人的眼前了。
随着她的呼吸,她的乳房上下起伏着。那两团白肉不大不小,结实而丰满。
乳头羞怯怯地凸起,上面的褶皱似是等待被抚平。
小蛮腰顺滑的线条,连接着修长的腿和浑圆的臀。
一双秀气的脚丫,脚趾微微翘起,整齐而白皙。
铁牛迫不及待地,大手一把抓住她的一只乳房。
用带着老茧的手指,揉撚着月娘的乳头。
仅是那细致柔软的触感,就已让他血脉贲张。
俯身用嘴巴叼住另外一只乳房,舌头贪婪地在上面吮着吸着啃咬着,像是再也不打算放开。
「你这蛮牛,她可不是你一个人的!」王大的手不客气地打落铁牛的手,像揉面一样地挤压着月娘无辜的乳房。
铁牛沈醉在月娘的乳房中,无暇与王大争执。不断用他的手和嘴巴,依次紊乱地蹂躏着月娘的一边乳头。
而王大则用他汙黑的指甲,刮弄着月娘的令一只乳头。
他把那小巧的乳头揪起来拎的老高,又把它用力按回去。
觉得这样不过瘾,他也开始用嘴巴亵弄。
他用牙齿啃着乳头,用舌头不断撩拨乳晕。
最后索性张大了嘴,几乎把月娘的整个乳房都含在口中,用力地舔着。
月娘的两只乳房,就被他们这样无情地亵渎着,上面都是他们的口水。
「嗯,哼……」月娘口中,发出一阵细碎的呻吟声。
她在昏迷中,感到有什麽东西,正侵犯着她少女的身体。
可她睁不开眼,沖不破黑暗,甚至喉咙里发不出完整的声音。
迷药让她浑身都丧失了力气,只能任由别人爲所欲爲。
她知道有什麽人正在玩弄她的乳房,那少女最骄傲羞人的部位。
那感觉像是两条蛇缠绕着她,不肯放过她。
湿腻腻的,又恶心又麻又痒。
可不知爲什麽,在那样的攻势下,她也模糊地察觉到一种快意渐渐升腾。
所以她呻吟出声了,她的乳房也胀大了。
甚至,那两只小乳头,也充血了,硬挺挺地耸立着。
上面的皱褶,也花朵一般地绽放开来,似乎渴望更多的亵玩。
「看这小骚货,奶头硬了。王大,看看她小穴流淫水没?我想马上就日弄她。」铁牛的肉棍被他释放出来,硬硬地摩擦着月娘的乳头。
王大恋恋不舍地放开她的乳房,毫不留情地掰开她的双腿。
又把床边的蜡烛掌在手中,靠近了月娘的阴户处,仔细地看着。
之见那里已被淫水所打湿,少女不甚浓密的阴毛,有几根被黏在阴唇上。
虽然月娘人是昏迷的,可她的身体,却还是敏感地,被他们激发出自然的情欲反应。
「流水了!还不少呢,真是个骚穴。咱们哥俩猜的还真没错。」王大的眼睛被少女的下体刺激的红了,他俯下身去,凑近了那隆起的阴户。
他贪心地嗅着,闻到一种甜腥的味道,那是少女自然的体香。
王大忍受不住那味道的诱惑,他的嘴巴也凑上去,用舌头拨开碍事的花瓣,直探入月娘的甬道里。
又是勾又是舔又是磨,还模仿着性交的节奏,一伸一缩地舔弄着内壁里的一处处嫩肉。
月娘的汗水挂在身体上,她感觉到什麽东西,进入了那羞人的所在。
她想挣扎,可是根本没用。
那东西不仅不撤出,反而变本加厉地侵占着她。
那东西残忍地侵蚀着她的理智,身体里有一种难耐的空虚感渐渐涌现。
她倒有点点希望,有什麽可以填满自己。
在那东西的搅动之下,她的下身突然间一阵不受控的收缩抽搐。
月娘竟然被王大的舌头,弄丢了身子。
「日!这浪货丢了,淫水喷了我一脸!」王大得意地抽出舌头,舔舔嘴边的爱液,淫笑着说道。
铁牛一直也没閑着,他看王大舔弄得不亦乐乎,也不好硬上。
只能用又硬又热的龟头,顶弄着月娘的乳沟和乳头。
让那腻死人的触感,满足他的渴求。
现在看到王大一脸的淫水,淫靡地闪着亮光,铁牛央求道:「大哥,让我先干她吧。兄弟实在受不了了,鸡巴都要绷不住了。」
王大笑笑,退出了月娘的两腿之间。「行,便宜你了,这骚货还是个处子呢。里面紧的要命,我的舌头都要放不进去,你就先开开路吧。我来玩玩她上面的那张小嘴,一定也很销魂。」
铁牛闻言大喜,来到月娘的两腿间,仔细地先看了看。
那小花穴还是紧紧地闭合着,但那条小肉缝中,仍在潺潺地流着淫水。
花唇湿哒哒的,像是雨后的玫瑰。
铁牛吞了口口水,把自己那根孩子小臂般的肉棒,顶到了月娘的穴口上。
他在穴口上转了几转,沾了些淫水,尝试着向里捅。
可那穴口虽有淫水的滋润,也竟像紧闭的大门,让他急的一头汗。
无奈下,铁牛捧起月娘的阴户,向上吐了一大口唾液。
又把她的两条长腿,结结实实地架在肩膀上。
这次,他沈了沈身体。
顿身将鹅蛋大的龟头,稳稳顶着那小小的穴口,用尽全力向里一顶!
这次,他的肉棒终于尽数没入了月娘的甬道内。
中途他碰触到一片薄膜的阻碍,他知道,那是处女的信物。
于是,他更爲亢奋,毫无怜惜地用力狂沖进去。
这人人豔羡的小美人儿,她的第一次,居然被自己得到。
铁牛想到这里,就更爲得意。
月娘被一阵极爲疼痛的感觉刺醒了。
那是一种尖锐而清晰的痛楚。下体被撕裂一般,体内有个东西涨满了她,刮蹭着她嫩嫩的内壁,塞得她下身好难受。
月娘知道,她的贞操没有了。
她好想睁开眼睛,看看是谁这样侮辱她,可她眼前是一片漆黑。
她很想大声呼救,可嘴巴里有东西塞住她的喉咙,她也叫不出声。
她想逃走,
可是两只手被禁锢着;
两条腿,被一个人的双手死死钳制住。
她哪也去不了,只能忍受着这样羞耻的强暴。
王大一边把玩着月娘的两只乳房,一边看着铁牛狂暴地奸淫着月娘。
他察觉到,月娘已经从剧痛中醒来。
于是他不怀好意地笑笑说:「兄弟,你慢着点。你那话儿太大,把这淫妇日醒了。怎麽样,她的滋味?」
铁牛气喘吁吁地,一面减缓了沖刺的速度,一面说道:「美死人了。骚穴里面又湿又紧,她还一个劲地使劲夹我,吸我,我的鸡巴都要被她吸进肚子里去了。真是个骚货!」
「慢着点,夜还长着呢。我们琢磨了她那麽久,要是一会儿就玩完了,浪费了哥哥的银子。那迷烟可不便宜呢。」
王大将月娘的两只乳房揉搓得发红,又用力挤在一起。
他也掏出肉棍,塞进那深邃的乳沟中磨蹭起来。
王大的肉棍虽然没有铁牛那麽粗壮,但却很长。
每次从乳沟里挤出去,都要蹭到月娘细嫩柔软的嘴唇。
月娘无声地流着眼泪,忍受着下体的剧痛,和鼻子前面隐隐传来的腥臊味道。
没想到宝贵的贞操,就这样毁在两个粗鄙的男人手上。
甚至,她不知道是谁强暴了她。
月娘越痛,身体的反应便越强烈,甬道死死地挤压着铁牛的肉棍。
铁牛生怕自己一个不慎就泄了出去,被王大所笑。
于是急忙停了下来,将肉棍停留在甬道里不敢妄动,可那甬道仍是火热地包围着他。
「太紧了。再操弄下去,我就要泄了。」铁牛用力顶着她的花心,肉棍上的青筋一跳一跳地,涨得月娘很难受。
大腿根处的处女血,已经要凝固干涸了。
在疼痛渐渐消退后,取而代之的,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。
「慢着点,这个淫妇,今天不干得她苦苦求饶,就浪费了我们这番心思。」王大一边玩弄着月娘的乳沟,一边回头对铁牛说道。
说完,他抽出肉棍,放开了那对被蹂躏得通红的乳房。
他俯身压倒在月娘的耳边说道:「贱人,你给我听好。现在,爷爷要操你的小嘴。你给爷爷乖乖地含住,好好地舔弄。舔的爷爷舒服了,我就饶了你。若是敢大喊大叫,或者想咬掉爷爷的命根子,老子就用匕首,豁开你这漂亮的小脸蛋和下面那张小嘴!听明白了吗?!」
说着,他用一把冰冷的匕首,在月娘的脸颊上来回地磨着。
月娘知道自己难逃此劫,又被他的话所威胁,只得流着眼泪,默默地点点头。
王大满意地笑笑,一手将匕首架在月娘的脖子上,一手将月娘口中的破布掏了出来。
月娘一阵剧烈的咳嗽,但还没等她平複过来,一条长长硬硬的男根,便迫不及待地塞了进去。
「舔!吸,好好地裹着它!」王大一把拽起她的头发,强迫她吞下更多。
月娘强忍着那种恶臭的味道,尽力张大了嘴巴。
她是个处女,从不知男欢女爱。
只能听从着王大的指示,怯怯地,用她细致嫩滑的舌尖,去轻舔和碰触那肉棍的顶端。
铁牛眼看着月娘的小嘴里,被填充了那麽长的一根肉棍,顿时淫兴大发。
也管不得其它,又开始了新一轮猛烈的沖刺。
他每一下都用尽全力,整个沖进去沖击她的花心;
又狠狠拔出去,把她花穴里粉红色的嫩肉,都翻了出来。
在铁牛的作用之下,月娘的上半身也随之蕩漾。
两个乳房一跳一跳的,刺激着两人的淫欲。
每一次铁牛的沖撞,都让月娘的嘴巴一收,把王大的肉棍包裹得更爲紧密。
她的舌头,也不由自主地碰触着王大的肉棍,和龟头上的马眼。
王大舒服得直歎气,觉得自己的鸡巴,就要化在这张小嘴里了。
他开始配合着铁牛的律动,每当铁牛进入的时候,
他就抽出;
而每当铁牛抽出的时候,他就阴险地钻得更深入,甚至碰触到了月娘的喉头。
月娘觉得一阵反胃,就想把口中的肉棍吐出去。
但王大偏偏用力压着她的头,把她更挤向自己。
他的肉棍上,早已沾满了她的口水和上涌的胃液,热热地刺激着他的兽欲。
「老实点,给老子吃下去,全都含住!」他压抑地低喊着,收紧了屁股,暴风骤雨般地顶着月娘的喉咙。
月娘喊也喊不了,叫也叫不出。
又被他死死压住,只能尽力放松自己,强忍恶心的感觉,让他多进入自己几分。
两个粗鄙的男人,就这样一上一下地,填充着她身体的两个小嘴。
月娘在这样的夹攻下,渐渐丧失了痛觉,像是失了魂一般被他们糟蹋。
渐渐地,她的下身开始泛起一阵新奇的麻痒感。
她不自觉地扭动了两下,不知道是想要铁牛进入更多,还是想让他快点退出去。
「操!这婊子来劲了,这麽大的鸡巴,还喂不饱她!」铁牛呵呵笑着说。
王大也卖力地抽插着月娘的嘴巴,回头看看说道:「这是个骚母狗。我的鸡巴这麽长,她都能吞下去,我都操进她的嗓子眼了。真舒服啊,从来没这麽舒服过。」
「是啊,能这样操她一夜,死了都甘心!」铁牛说着,低吼一声,决定自己要尝到那最舒爽的滋味。
于是他加快了节奏,啪啪地敲打着月娘的圆臀,咕叽咕叽的水声充盈室内。
两人的结合处,早已是一片泥泞。
月娘的淫水和白带混在一起,她的花穴早已被铁牛操的精湿一片。
淫水不仅弄湿了她的菊穴,也沾上了铁牛的肚皮,连那两颗肉球上都沾得到处都是。
此时,铁牛一番飞快又大力的抽插。
她的淫水更是喷涌而出,半张床褥都像是尿过一般。
「骚货,浪屄。操死你,爷爷操死你。说,爽不爽快!」铁牛一边发狠地操她,一边用最难听的话去辱骂她。
月娘呜呜地哭着,嘴里还含着那支长长的肉棍。
王大也想听她的淫词浪语,于是暂停下来,用力扯着她的头发说:「说,说呀你,淫妇!」
月娘被身下那根肉棍刺得麻痒难耐,一心渴望结束那种痛苦。
又加上王大的虐待和恐吓,于是她只得违心地点点头,含着肉棍模糊不清地说:「爽快,快一点,求你再快一点。」
铁牛听到身下的女人这样的哀求,自然是卯足了劲。恨不能把自己整个人,都钻进她的小穴中去。
而那王大,也抓住她两侧的头发一起发力,用力挺着肉棍,强迫她一次次吞下她根本难以容纳的长度。
月娘在这难耐的折磨中,开始模糊地呻吟,说些毫无意义的话。
她在铁牛碰触到甬道内某处柔软的嫩肉时,突然受不住似的呜呜叫喊起来。
一阵强烈的收缩,一波波地夹着铁牛的肉棒。
月娘像尿了一样地,泄出了一身的阴精。
铁牛被她这样一喷一夹,强行控制的能力消失殆尽。
他最后用力一挺,火热的精液都灌进了月娘的子宫内。
而月娘的嘴巴和舌头的收紧,也同样让王大乐不可支。
最后几个耸动之后,他也把一大泡精液,射进了月娘的喉咙里。
月娘身下的花穴还兀自收缩着,嘴巴里觉得呛人的难受。
她想吐出去,却被王大的鸡巴死死堵住。
于是她只得费力地咽下去,剩下那些没来得及咽下去的,有些竟从她的鼻孔里溢了出来。
「妈的,还想吐出来。都给老子咽下去!便宜你这骚货了,这可是老子的精血,还不领情?!」王大看到月娘被蒙住眼睛,两只手腕都被麻绳勒出了血痕。
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,倒激发了他心内潜在的虐欲。
月娘流着泪,一言不发。
以爲这漫长的折磨终于到了尽头,谁知王大的肉棍一直深埋在她喉咙口处,被她几下吞咽的动作,又弄得渐渐硬了起来。
月娘心中十分害怕,她知道那意味着自己的苦难无法完结。
趁着王大终于松开了她的头发,她才逃脱了那根淫湿的肉棍。
费力地急促喘息着,嘴角还残留着浞白的精液。
身下的铁牛,从月娘结实的小腹上支起身子。
刚才排山倒海般的快意,让他倦倒在她的小腹上。
现在他也缓过乏来,那粗壮的肉棍,仍藏在她的体内不肯抽出。
他掰开月娘的双腿,撑到最大限度。
月娘少女的身躯格外柔软,此刻被他弄得两腿大张,成了个一字型。
她最娇羞的花朵,就这样明晃晃地,展示在铁牛眼前。
之前他只顾快点进去,发泄自己的兽欲。
事后才觉得,没能仔细好好看看这小美人儿的下体,是个损失。
铁牛端过烛台,就放在月娘的阴户附近。
借着烛火,他看到月娘的甬道,被自己的肉棍撑得几乎变了形,夸张地向两侧扩张着。
精液混合着她的体液,一点点从肉棒边缘溢出,把她的阴毛沾染得汙湿一片。
铁牛稍稍退出一点,以便更清楚地瞧瞧她。
随着他的动作,月娘又爆发出一声轻呼。
铁牛兴奋地,向那小小的花核上拍了一把。引得月娘的两腿不自觉地战栗,那花缝也随之收缩了一下。
处女的血,凝固在他的腿上和肚皮上。也映衬着月娘的双腿,愈发白嫩娇弱。
像是揉碎了一朵美丽的花,铁牛心里涌上一种莫名的满足感。
看着月娘随着呼吸轻轻开合的肉缝,铁牛始终没彻底拔出的那根肉棍,再次撑满了月娘的幽洞。
感受到铁牛又再蠢蠢欲动,那根肉棒缓缓地摩擦着她的内壁,月娘心底绝望异常。
她呜咽着说:「求求你,不要。我好痛,不要了……」两只手徒劳地挣扎着,想要坐起来。
却被王大一把按住,扯着她乌黑的长发,跌落回床头。
「婊子,别乱动。你以爲大爷是吃素的,干你一次就完事了?太瞧不起爷爷了。今儿要不弄你一整夜,就算爷爷白长了这根枪!」王大看她还在挣扎,擡手就给了月娘一个耳光。
月娘耳边嗡鸣着,嘴角溢出一丝鲜血。
做惯了粗工的王大,根本不知何谓怜香惜玉。
那只粗糙大手的力道,让月娘几欲昏迷过去。
她丧失了反抗的能力,但她残留的一点听觉,听到王大嘿嘿笑着对铁牛说:「你也是换个地方玩玩。她那小穴,现在也该归我了。你,上来,试试这张小嘴。你那麽粗大,尽管塞进去,保证让你飞上天!」
铁牛闻言心里痒痒的,但还是恋恋不舍地,又用力沖刺了几下。
他缓缓抽出自己已经再度暴涨的肉棒,一股精液流了出来。
铁牛看看月娘吃过王大精液的脸,上面还挂着几丝。
于是不甘示弱地,用手用力压了一下月娘的小腹,更多的精液潺潺流了出来。
铁牛大手掬起一大把精液,就和王大换了体位。
他用手指拨开月娘微张喘息的嘴巴,就把手中的精液,一股脑地倒入。
月娘昏沈中,再度尝到那呛辣的味道。
她无力地咳嗽着,本能地抗拒着。
铁牛的精液也被咳了出来,溅的她一脸都是。
铁牛火大了,月娘居然不肯吃他的?
他粗暴地用手指刮着月娘脸上喷出来的精液,用力地把四根手指都塞进月娘的小嘴里,逼着她舔干净。
「给老子吃下去!」他一面低声威胁着,一面用另一只手的指甲,用力地掐着月娘的乳头。
月娘的乳头被他捏的几乎扁掉,那种钻心的痛,迫使她乖乖地舔弄着铁牛的每一根手指。
细细地从他的手指根部,一直舔到指尖,连手指间的缝隙都没放过。
她一边舔着吸着,一边苦苦哀求:「爷,求您放过我吧,我好疼……」
铁牛的手被她这样细心地伺候着,看她听话地舔干净所有精液,铁牛舒服地长嘶一声。
另外那只手终于渐渐放松了对乳头的虐待,开始轻撚细揉起来。
她的小舌尖舔过他指缝的时候,那种腻死人的舒爽和麻痒,让他的肉棍再度胀大一圈。
粗壮犹如孩童手臂的肉棍,现在已经贴着肚皮,凶猛地蓄势待发了。
上面小眼上,也流出了晶亮的体液。宣示着他的欲望,已经无法再等了。
王大的手指,此时也没閑着。
他一面看着铁牛玩弄月娘,一面用最粗长的中指,在月娘的幽洞里反複穿插着,画着圈。
月娘每次承受不住的时候,就想把腿闭紧,拒绝这种羞人的亵玩。
王大的手指像他的肉棍一样,又长又灵活。
那样地插弄她,让她又疼又痒。
可王大一看到她想闭合双腿,就会用手指狠狠地弹她的阴核。甚至用食指和中指夹着她的阴核,用力向上拔。
月娘的上身和嘴巴被铁牛玩着,下身被王大玩着,她简直不知道该求哪一个住手。
她也明白,无论哪一个,都不可能对她手下留情。
于是她只能认命地,「呜呜」低鸣着,啜泣着。
惧怕王大虐她的花核,月娘强忍着花穴里传来的奇怪搔痒感,不敢再闭合双腿。
她的双腿瘫软地大开,她的阴户就那样暴露着,任由王大勾插缠磨。
王大得意地淫笑着,不满足于一个手指享受她的紧窒肉壁。
于是吸了口气,把四根手指,统统塞了进去。
那种几乎被撕裂的感觉再度袭来,月娘下身抽搐着,上面的嘴巴也跟着用力,狠狠吸着铁牛的四根手指。
上下都被那麽多指头插着,月娘觉得自己的身体都要裂开了。
可铁牛逗弄她乳头的手,却让她的幽穴,加深了一种想要什麽东西探入的渴望。
王大的手指关节又硬又大,刺得她娇柔的内壁好难受。
他就那样不吝啬力气地,掏着她的花穴。
四根手指一会儿并拢,一起挠着里面的小突起;
一会儿又邪恶地分散张开,各自划磨着敏感的内壁。
「不行,我不行了,别这样。呜呜……」月娘终于不堪忍受这种折磨,吐出铁牛的手指哀哀乞求道。
「骚货,那就说点好听的,告诉爷爷,你想不想被爷爷的鸡巴插?快说!要不就没完!」王大和铁牛相视一笑,长指又在月娘体内勾挑了一下。
「想,我想……」月娘本是个黄花姑娘,怎麽能说出口,只好含糊地说道。
王大却不能满意,他抽出手来,用巴掌使劲地向月娘的阴阜拍打,拍得月娘疼痛求饶。
「想不受罪,就老老实实地喊出来,叫出来,叫到大爷满意!否则,我们玩完了你,就把你扔在这里不管。让卫府所有人都知道,你被操是个什麽样子!」
月娘甯死也不愿这样赤身裸体地被大家发现,她只好抛开少女的羞耻感,按王大要求的那样低呼:「爷,我想让你……操我,插我,想被爷的鸡巴,用力地插,快点插我,好难受!」
月娘带着哭腔的淫叫,终于满足了两个男人的听觉享受。
王大和铁牛对了个眼神,各自拿起自己炙热如铁的肉棒,一齐插入了月娘的两张小嘴内。
铁牛的粗壮,瞬间塞满了月娘的口腔。
他硕大的龟头,堵住了月娘的喉咙。
月娘几乎难以喘息,就要窒息了。
她只有用力仰头,让自己的喉咙更多地接纳大肉棒的沖击。
鼻翼用力地张着,贪婪地吸着空气。
她的嘴巴又酸又痛,被撑开到了极限。
铁牛不留余地地按住她的头,抓着她的头发,疯狂地犹如捣蒜般地,捣着月娘湿热的口腔和舌头。
每次都顶入她的嗓子眼,去摩擦那销魂的喉头小肉。
不一会儿,月娘的嘴角便已撑裂了,细细的伤口渗着血丝,更添凄美之态。
她承受着铁牛比王大更爲暴虐的抽插,连叫也叫不出声了。
王大则享受着月娘因紧张和疼痛,更爲紧窒的蜜道。
那里时不时紧缩着,挤压着,蜷握着,蠕动着。
像是有无数孩童的小嫩舌,一起吮着他的肉棒。
王大呼呼喘着气,挺腰动臀,一次比一次更爲深入地插着月娘。
恨不能插穿了她,插爆她的花壶。
每次因爲月娘的紧缩而差点泄身的时候,王大就会大力拍打月娘的圆臀,不知是赞歎还是警告。
大手把她浑圆结实的臀部,拍打出清晰的红手印。
王大盯着月娘的乳房,觉得那里波浪般涌动着,不该被浪费掉。
于是他用力一顶,又迅速抽出,惹得月娘一声闷哼。
「别急,浪货,待会儿好好收拾你。」王大说着便跳下床。
「做什麽去?正到紧要处!」铁牛疑惑地问,身下的动作却不曾停止。
月娘蒙着眼看不到,心中更添一份恐慌。
王大摆摆手,径自走向织布机,顺手扯下几段极细的长丝线。
又看到一旁的梭子,也攥到手里反身回来。
铁牛不知道王大想做什麽,他眼睁睁地看着王大用力抻了抻手中的丝线,靠近了月娘的胸脯。
「你先停一下。我有个主意,好好玩玩这小婊子。」王大拍拍铁牛汗流浃背的身子说道。
铁牛也有点累了,于是好奇地停下来。暂时抽出了肉棒,不眨眼地看着王大。
月娘的身子,已经被折磨得成了鲜丽的绯红色。
细密的汗珠,在她的额头上和胸脯上沁出来。
尤其是乳沟部位,密密麻麻一层小水珠,更像是被雨打后的梨花了。
既绮丽,又娇羞。
王大拿着手中的丝线,凑近了月娘的乳头。
挑亮了烛火,把两根韧度很高的红色细丝线,都绑在了月娘的乳头上。
月娘只觉得胸前一阵刺痛,并不知这人到底想做什麽。
但她直觉就明白,这一定是折磨她的新花招。
「嗯」,她不敢说什麽,生怕招来更多的报複,只是不安地扭动着身体。
王大知道她害怕,于是用力把丝线缠的更紧。
把她的一对乳头,都用细丝线绑得紧紧的。
他恶意地轻轻一拽那两条丝线,月娘忍不住痛,轻声叫了一声「痛。」
铁牛饶有兴趣地看着王大的妙想,又听到月娘勾魂的呻吟。
忍不住俯下身去,伸出舌头舔月娘的嘴唇和牙齿,把她的呻吟都堵回去。
月娘徒劳地躲避着,舌头不肯与铁牛热烘烘的唇舌纠缠。
可铁牛却吻得来了劲头,捏住她的下颚和脸颊,强迫她接受自己。
轻而易举地就捉住她的丁香小舌,吸奶一样地吸吮她的舌头,不让她逃脱。
这时,月娘的乳头被王大手中的细丝线牵引着,勒得充血,更爲硬挺地挺立着。
原本粉嫩的乳头,此时已经成了诱人深沈的紫红色。
王大把两条丝线握在手中,返回到月娘的两腿间。
高高举起她的一双美腿,再度把两条丝线的另一端,狠狠系到月娘的两个大脚趾上。
细丝线刻意被绑得很短很紧,月娘胸部越发刺痛。
只好更高地擡起双腿,减轻乳头的牵动引发的疼痛感。
王大看她果然把腿和屁股翘得更高,他此刻不止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花穴,更清楚地看到月娘的后庭,就暴露在眼前。
她的菊花粉嫩干净,因爲姿势的关系,那些细密的小皱褶都被撑开了多半,看起来更爲圆润可爱。
菊穴周围还长着浅淡稀疏的一圈绒毛,王大用食指捅了捅,那菊花顿时像受惊一般地缩起来,隐没在臀缝中。
「淫货,一会儿就日你的小屁眼。身上这几个洞,爷一个也不浪费。」王大狞笑地说着。
毫无预警毫无润滑,突然扒开月娘的臀缝,看準那处菊穴,把手中的梭子塞了进去。
「啊!」月娘一声大叫,吐出铁牛的舌头,头摇摆着嘶哑喊道:「不要,不要,拿出去,求你拿出去,痛,痛死了!」
铁牛吓了一跳,忙捂上她的嘴巴,制止了她的哀求。
月娘的眼泪扑簌簌低落,一会儿就把枕边的床单都湿透了。
铁牛回头一看,被那绮丽的景色震住了。
两颗紫红色的乳头,牢牢跟她白玉般的大脚趾系在一起。
她越想挣扎,把那梭子挤出去,可胸前的疼痛又逼着她,把脚擡上去。
倒让王大把那梭子塞得更深入,只剩下尖尖的一头,露在菊穴外。
菊穴已被那梭子所伤,边缘的皮肤也破了,渗着丝丝血迹。
王大不管不管月娘的痛苦,就着她自动擡高的双腿,把硬到极限的肉棍,一鼓作气地,全部捅进了月娘的甬道。
她的小穴更紧了。梭子在菊穴里霸道地侵占着她,王大的肉棍就隔着一层薄薄的皮肤,开始了在她小穴里的沖刺。
月娘陷入了地狱般的境地。
铁牛粗壮的肉棒,堵住她所有的痛楚哀鸣。
他发疯一般地,把她当做一件没生命的器具那样,用胯间的猛兽,捅着她的咽喉。
身下的王大则欣赏着她上不去下不来的苦楚,发狂地在她体内插着,转着圈地挑逗着她。
还时不时地拽那两条红丝线,让她的乳头也不得安甯。
操到兴头上,王大索性把那梭子又拽出来,再捅回去,肆虐着她的菊穴。
丝丝血迹和肠液,透过梭子的空隙,流的他一手都是。
他用这梭子,开发着月娘生涩的后庭。
期望她过一会儿,便可以接纳他更爲巨大的肉棒。
月娘的身体已经不是她自己的了,她麻木地承受着,全身到处都被淩虐着,让她不知哪一处最痛。
终于,铁牛和王大经过漫长的第二轮抽插,分别在她的穴内和嘴里,又射出了大量浓稠腥臭的精液。
月娘此时一如一具玩偶,只能大口呼吸着。
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活着,还是已经死了。
她连流泪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花穴里汩汩冒出的精液,润滑了她的菊穴。
那被插进去的梭子,也终于被月娘的本能反应,挤出了体外。
王大和铁牛都趴在她身上歇乏,没有解开丝线的意思。
月娘还维持着那最耻辱的姿态,两手腕挣扎得磨出了更多血泡。
一双腿蜷缩在乳房上,两只脚尖几乎触到她自己的耳朵。
而她的乳头,已经紫得发黑了。
乳头的体积也凭空增大了两倍,像两颗熟透的葡萄般,颤抖着,挺立着。
月娘被折磨的半死,而两个男人则累得半死。
三个人谁也不出声,都只是喘息着。
谁都没发现,这间小小的石屋外,被捅漏的窗子后面,又多了一双泛着霭色的眼睛。